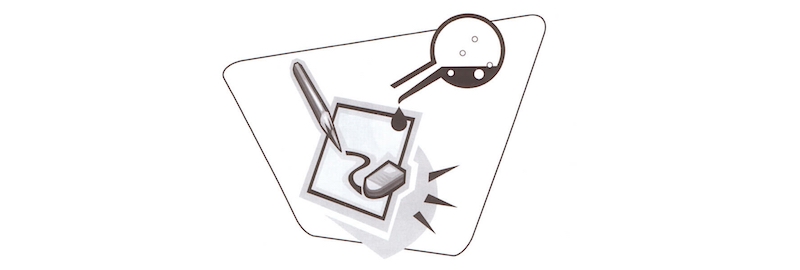公元 100 年左右,距今近二千年前,東漢宦官蔡倫以樹皮、破布造紙,是我國四大發明之一。本刊同文 James 先生在上期的「潘勛與他的欲望植物園」中引了他老師的話:「犧牲上好的樹林,去印垃圾。」用以警惕自己寫作要認真,令人欣佩。他提及書是用砍下來的松竹林製成的紙印出來的。然則由林怎樣變成紙呢?讓我想起了三十年前,與造紙有關的一些往事。那時,我適在美國西北地區林業翹楚「惠好」公司(WEYERHAEUSER)工作,同事中有幾位華人科學家,想光大先人,從事過造紙革命,可惜功敗垂成。
美國的森林大部分國有,惟平均每一方里的私有林,惠好就有一畝,為數不小。惠好在自己的林地裡運作,砍了種,種了砍。砍下來運到下游工業如木材和紙槳等工廠,從事生產。惠好的林場與工廠,雖然遍佈北美,但也學美國石油的利己政策,盡量先標購別人的森林來砍。
當六、七十年代經濟繁榮時期,在惠好公司的科技中心工作的科學家有一千四百人之多,華人約占十分之一。他們把松子拿來分析交配,加進化學成分,培植出新的品種。經過育苗場試驗成功後,在自己的林地裡,每年種植超過一億株。樹木在自然環境下生長,需七十五年成材。況且枝節橫生,又遭蟲害風折,到砍下來時,能用之材不過一半。而科研培植出來的新樹,既防蟲又抗風,主幹挺直無枝,到樹巔才枝繁葉茂,成長期僅需二十五年,可用材達 95%。由此可見,科學林的經濟效益比自然林高六倍。不過,自然林的木質因成長期長,比科學林好。
砍了自然林再種新品種的樹,叫第二代商業林。提到商業,難免要講效率和效益。於是砍樹就和剃小平頭一樣,一次過剃光(crew cut),所以我們常在郊外看到一座座光禿禿的山頭。用來造紙的樹木分兩種,印書的紙多用軟木(softwood),如松(pine)和樅(fir);粗紙如超市的紙袋,其成分則以硬木(hardwood)為多。科研品種以樅為主,既能造紙,也可用做木材(lumber)和三夾板(plywood)。砍下來的樹,去枝取葉,先進集散場,再按材分發。造紙用的原木,先運到木片廠切成小片(chip),再送至紙漿(pulp)廠。做成紙漿后,烘干壓縮,才送紙廠,再還原為漿造紙。
造紙的重要階段在於造漿。因為,老法是將木片在溶化爐中,添水加熱,加入硫磺,溶解成漿。但是用過的廢漿,放出來破壞自然生態,受到政府的嚴厲處分,罰款以數十萬計。為此,幾位華人科學家發明了反傳統的造紙術,不用化學法,改用機械法(Thermo-mechanical)。木片在高溫水中煮軟,用機器把它軋碎溶化為漿。這樣,排出的廢水就不會有污染了。
惠好以為得計,斥巨資建廠,用新法從事生產。料不到的是木質的纖維在高溫壓碎時斷了,紙張因而失去了韌性,易於破裂。造出來的紙沒有人要,於是多年的心血化作一場春夢了。我們的科學家這次失敗了,最後逃不了「成王敗寇」的鐵則,被遷散了。現實是多麼無情呀!但是更無情的是八零年代經濟衰退,公司因為研究單位既化大錢,又難有立竿見影的績效,一下子辭掉了科研中心一千多人。華人自然也不例外。這百餘位同胞便像同林鳥一樣,「大難來時各自飛」了。這個造紙的小故事也許還有「一得之見」,希望不是「印出來的垃圾」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