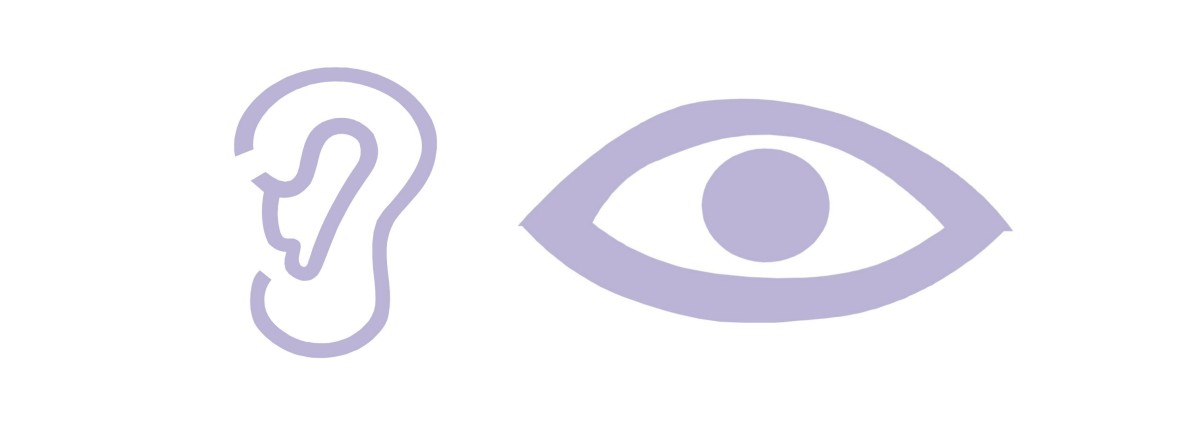兒時,大人一邊比劃一邊教:「嘴臉鼻子耳朵眼」。如此這般認識了五官。
對鏡梳頭,順便瞄一眼正面那四官,沒長兜風耳,忽略左右聽官的窗葉,少了關愛。其實不盡然;五官中同它們這一雙淵源最深。初學寫姓時總聞:「陳的耳在左,東在右。」學母親那個鄒字便聞:「耳朵在右邊。」人都有兩隻耳朵,那些「字」偏只一耳,叫人無所適從。不過樂趣也有,母親叫不動我們時,打著四川話:「講話都當耳邊風呀!」或:「你們一個個的耳朵都賣到燒臘館去了呀!」這時心中喜孜孜,暗自樂著。少長,讀高爾基,他說:「我們有兩隻耳朵,卻只有一張嘴,讓我們多聽少說。」口才木訥,禍根所在。
青春時代,長長青絲半遮面的時尚,我嘗試過,但受不了,總是爽爽然把頭髮撥到耳後,似乎這樣才能昭示出「聞」的重要,具備海納百川的實力,兩耳盡聞天下事了。有一點是肯定的,從不傷害他們,連揣摩的念頭都無,一腦子的否定和拒絕。因此上世紀六十年代初,西風漸進,臺灣的女性為裝扮而打耳洞時,我這廂是欠奉。生長在抗日戰爭的烽火聲中,年青人不分男女報國心切,即使當時大後方的重慶,也不見知識青年穿耳洞的。現在注意從中國來的我輩人,很少有穿耳洞的,毛澤東閉關政策使然。再說家中上兩代人,祖母和母親都是穿耳族。可能是承接了父親祟尚自然的家風,我家四姊妹到白頭,無一人耳朵穿過孔。而我們的下一代小小年紀就忙著打扮,耳朵早受難了,至於孫輩,打起孔來是一連串,耳葉上的穴位全毀,美得來叫我這個古老石有些兒懷疑了。
首先是看見銀幕上,香港女星林翠戴了真珠耳飾,緊緊地貼在耳上,感覺煞是美。流行像流水一般快,那陣子見某某也去穿了耳洞,又聽某某因穿耳洞發了炎。愛美是天性,戴耳飾有,但我也是後知後覺;婚前有次被帶去參加先生單位的聚會,當時宣稱有份禮物要送出,沒男士的事,唯在場的太太小姐有機會得到,由大隊長夫人抽出,剎那間欣聞自已的名字,跟著跑上前接過獎品。禮物是一尺見方,用五十年前少見的花花紙包裝,拿在手上感覺很輕,打開,大盒中間塞了雙紅花耳環,是那種夾耳使人痛的。婚後閒談,提到中獎事,他才透露是主辦人商量好,有意叫我得到的,因他們察覺到,我未戴過耳飾,觸發了照顧年青人的心。跟隨潮流無法擋,這溫馨事件後,那種轉螺絲便能夾住,又不傷耳根子的行頭是我最愛,收集隨年月增加,標緻、迷人、多姿多彩。同樣可以美將起來,覺得必要,又遇上好心情,配衣配裙的裝扮,自是不免融融自樂。有時因物連帶被發現,耳葉下位生得溫厚,得到讚賞,又加一樂。
這兩扇窗葉內的世界,無從親眼目睹,曲折細緻,大門盡敞,二門黑洞洞,專家還得借助儀器探測內裡玄機。有人耳內潮濕,我倒好,一籠子乾耳,耳泥多了頭一偏,就自動幌了出來,無需搯耳。近來老邁,淋浴後喜歡往床上躺躺,誰知竟造下了中耳痛。第一次犯時心中納悶,未患感冒怎麼會?左思右想得出結論。毛病出在浴後馬上躺床,沖完澡外耳不免有少許積水,人橫躺下水流入中耳,積水發炎之故。幸好先有微痛徵兆使人警覺。繼而想起四十多年前,兒子得中耳炎的往事:孩子不足一歲,有日哭鬧得厲害,帶去鎮上看醫生,醫生是從日本學成返回的臺籍人士,他檢查兩耳後,什麼藥都不用,說感冒鼻水流入中耳,叫我橫抱在懷裡,他用一盞小燈,隔三寸的距離,對著耳洞乾烤,瞬間孩子就平靜下來,漸漸睡著了,大概烤廿分鐘,便讓我們回家,第二天再烤一次就好了。從此見有孩子感冒哭鬧,就告之試用此法,蠻靈驗。如今用上這一招,給自己烤一烤。咳!真是烤得十分自在,躺著烤都睡著了,耳痛不藥而愈。幾次不小心都及時自療,不瞧醫不吃藥,好了。這下緊記心頭,淋浴後用一棉簽吸水,躺下享受就無妨了。人生一絲半縷的經驗,並非無足掛齒,留與後生者也是好事。
話說人吃飽後,嘴巴閒著沒事,思考整個身體全靠自己不斷輸入食物才支撐住,勞苦功高,為何鼻子偏居上?便提出抗議。鼻子「哼」了一聲說:「若不是我辨別香臭,你能吃嗎?」這一說神氣起來,正要往上交涉,眼睛放話了:「沒有我,你這個鼻子早碰扁了。」以上是個杜撰的故事。眼睛的確是高高在上,明察秋毫,就連狗眼還看人低哩!
童年見長睫毛的大眼,彎彎的笑眼,一動似會說話的靈眼,都羨慕得很,只因自己缺。感謝老天爺有眼,念我苦心,婚後第一胎就得了個大眼娃,一雙眸子又大又明亮。抱在臂彎,牽在身旁的日子,孩子一雙眼晴常吸引路人。那陣,臺灣年年中國小姐選得熱鬧。叫方瑀的連方瑀,真是萬人迷。不只一次,有人走近,慎重地告訴我說:「這是以後的中國小姐」。心喜也警惕地擔心過。其實眼小無妨,丹鳳眼即是,與大眼較,風彩各異,秋色平分。不說別人,我家小孫女有雙小眼晴,兩三歲時,她的眼睛一眨跟著飄過一邊,別有韻味,表達了她的心態。那種眼神,看著叫人好笑和詫異。她周圍的我們,無一有此動作,不明就裏,貶眼代替了言語,唯有判定她上輩子是演員。古人說:「山不在高,有仙則名,水不在深,有龍則靈。」我說:「眼不在大,有韻則靈。」
靈靈的靈魂之窗,我倒有一則美美的經歷。某日我的舊鄰,一位十分可愛的太太,人人稱她美人的。在臺北宴客,我被邀請,進得門來,大廳中已經來了不少人,我要先向主人打個招呼,驀地裡見大貓咪似的眼睛向我走來,趕緊迎上去,原來美人戴了人工睫毛,既黑且濃,又長又捲。我可樂開了,直楞楞瞪著她瞧,輕輕對她說:「今天還掛了窗簾呀!」她眨著眼睛告訴我是美容師的傑作,絕對是傑作。平常人眨眼無人注意,戴了這種睫毛,眼睛貶有如舞臺上炸開的燈。何況美人當天是焦點人物。真不愧是大師出招。這種稀有的進口貨剛流行,我住在桃園眷區,小地方閉塞,不知大城市已有先進們使用。心想西洋貨是為外國人設計,別人眼睛夠大,貼上不致如此的誇張和過份。誰知有回見報紙登出大明星 碧姬巴度的像片,一雙大貓眼的扮相,是同樣的誇張,一樣的過份。因此這輩子都不曾跟進過。近日看了湯顯祖的牡丹亭,四百年前他的戲曲裡就唱出:「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自然」。而現代人的打扮是標新立異,眼上、睫毛上灑金粉不為奇,近日在電視上更見一雙雙彩色睫毛,各出花招,靈魂之窗早裝點得繽紛多元,淋漓盡致了。
說相聲者問:「為什麼戴了假睫毛心裡沒有負擔?」答的人說:「因為是戴在別人眼上。」的確,會舒服嗎?人的眼睛容不下一粒小沙,流下眼淚是揉是擦都得小心。我小時候體弱,被說成是最愛哭的孩子,可能淚流太多,成長後有一雙欲哭無淚的乾眼,也種下眼睛的病症。如果此一說法不能成立,我還有一個確實的原因,曾經被強烈的水壓射在左眼上,那種「眼冒金花」的奇境,我是見證過的。卅歲就得配老花眼鏡,初期只有看書讀報才戴上,不久便加了一番,有了散光。從此是鏡不離眼的全天侍候著。三十出頭戴老花眼鏡是早了些,但有好處,可以遮擋初發的皺紋。鏡片的尺寸合適還可以模糊眼袋的存在。不久前我的甥女回臺灣做眼袋手術很成功。用的是李登輝夫人的美容醫。可見人們多麼看重自己的雙眼,對這一點,我是失責了。以前不管是靠是躺,閒書在手就不讓兩眼休息,那裡還顧了它們的形像!四十多歲無緣由就見眼白一片血紅,看著怕人,但不痛不癢,還會自動淡去,偶然遭這麼一次不傷大雅,也就沒去管它。五十歲時,兒子學了中醫,給我開了中藥吃(關沙宛煮內仁肉,吃葷的可加瘦肉一塊)。吃後情形大大改善,泛紅不再。然而好景不常,左眼得了夜盲症,天一暗就瞎了,總望「不叫人間見黑夜」。否則矇矇矓矓迎接黃昏, 並趕緊往屋內跑,有燈光就好。
相信一切有定數,要來的逃不過,所以從不作身體檢查,但身邊的人好意,有次被說服了去檢查眼睛。醫生一量眼壓,緊張異常,馬上不停地給我點藥水,說眼壓太高會瞎,那個下午我任由他辦,一連的各種眼藥水滴在左眼裡,澀澀黏黏酸酸,幾個小時才放我回家,那時左眼真是瞎了,連牆上的裝飾全不見,只是一片白色。心中平靜,想瞎也只一隻眼,再想瞎了應該是一片黑,不該是一片白才對,人也「倒姑」的累了,回家好好睡覺去。過兩天再去見醫生,視線恢復就訂了日子做雷射手術,左右兩眼各打一洞,並定了我的是青光眼病(我自己認為只是夜盲,不過西醫說的青光眼有許多不同的症狀),兩種眼藥天天點,到死為止。手術後,乾眼及夜盲症都迎刃而解,只留下一種後遺症,左眼的瞳孔不能快速適應光的強弱,從陽光中走入室內,一時間全得靠右眼了。我是最不愛戴墨鏡的人,也勉為其難架上眼。其次去電影院就麻煩,幸得電視助我,不至忍痛犧牲這等娛樂。至於讀報看書也要收歛,不可一連數小時而為了。
想想活一輩子,眼睛為我帶來了多少樂趣,早上一睜眼就為我服務,所以各種器官裡,它老得最早!敬老唄!聽醫生的話一天為它點三次藥也是應該。